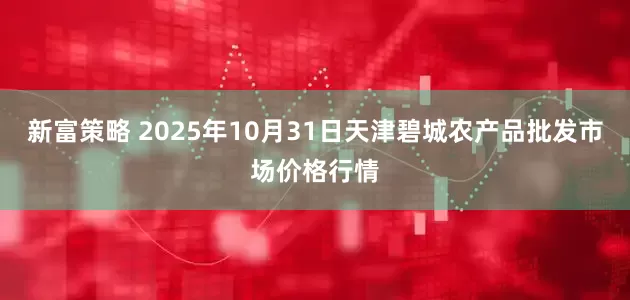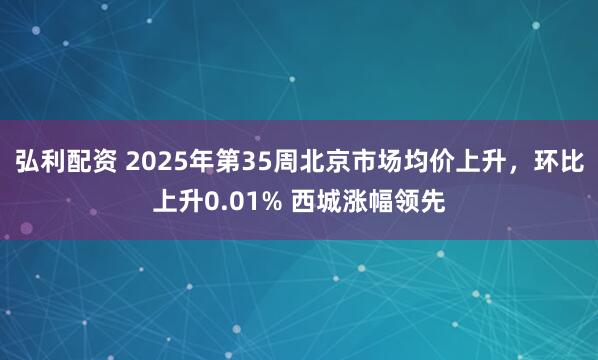*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银铺子配资
T-DXd为non-pCR的HER2+早期带来高效治疗新策略
金秋十月,全球学领域瞩目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在德国柏林隆重举行。作为肿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平台之一,ESMO大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临床实践的革新与治疗理念的升级。在本届大会上,多项改变临床实践的重磅研究结果相继公布,其中德曲妥珠单抗(T-DXd)的III期临床试验DESTINY-Breast05(DB05)的中期分析结果(摘要号:LBA1)尤为引人注目,被遴选在全体会议主席专题讨论会(Presidential Symposium)上发布,彰显了其卓越的学术价值和临床重要性[1]。DB05研究首次头对头比较了T-DXd与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用于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病灶的HER2阳性(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辅助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其结果的发布,不仅代表了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有望为这一患者群体的治疗策略带来根本性变革。
值此重要数据公布之际,医学界肿瘤频道特邀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龚畅教授、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李杰教授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过兆基教授共同参与ESMO现场圆桌访谈,围绕DB05研究展开深度对话。与会专家不仅深入解读了研究成果,还分享了对于HER2+乳腺癌治疗格局的深刻洞见。
龚畅教授
回顾T-DXd的探索征程,其在HER2+晚期乳腺癌的后线乃至一线治疗中,凭借其高效的“旁观者效应”和高药物抗体比的设计已展现出显著临床获益,并不断改写治疗标准。同时,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如果这样一款强效药物能够前移至以“治愈”为目标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对于那些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病灶、复发风险极高的患者,是否能够带来更大的根本性突破?DB05研究正是承载这一期待的关键试验,直接向现有标准治疗方案T-DM1发起了挑战。基于本次ESMO大会上首次公布的DB05研究数据,T-DXd在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展现出了哪些关键的疗效与安全性特征?其中哪些数据最令人印象深刻?
李杰
教授
HER2+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20%,是一种侵袭性强、预后不良的乳腺癌亚型[2]。对于HER2+早期乳腺癌,治愈是治疗的终极目标。然而,在接受新辅助治疗后,仍有近半数乳腺癌患者存在残留病灶,此类患者面临显著的疾病复发风险[3]。即便在术后辅助治疗阶段接受了强化治疗,部分患者仍会进展为转移性疾病。一旦发生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将从近90%骤降到约30%。因此,开发创新的早期乳腺癌治疗策略,有效控制疾病进展风险,对改善这类患者的长期临床结局有重要意义[4,5]。
DB05研究是一项III期随机、多中心、开放标签的临床试验,首次直接比较T-DXd与现有标准疗法T-DM1在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浸润性病灶的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辅助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共纳入了超1600例患者,按1:1随机分配接受T-DXd(5.4mg/kg;Q3W;共14周期)和T-DM1(3.6mg/kg;Q3W;共14周期)治疗。主要终点为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期(IDFS),关键次要终点为无病生存期(DFS),其他次要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远处无复发生存期(DRFI)、无脑转移复发间期(BMFI)和安全性。截至2025年7月2日,T-DXd组和T-DM1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29.9个月和29.7个月。

图1 DB05研究设计
在入组人群上,DB05研究的两组患者基线特征基本平衡,中位年龄约50岁,近一半的患者来自亚洲地区,30%左右的患者为激素受体阴性(HR-),50%左右的患者发病时为不可手术状态,超80%的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后腋窝淋巴结病理学检查呈阳性,78%左右的患者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的双靶新辅助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与T-DM1组相比,T-DXd组3年IDFS显著提高了8.7%(92.4% vs 83.7%;HR=0.47;95%Cl 0.34-0.66;P<0.0001),显示出具有高度统计学差异及临床意义的改善。T-DXd在所有预设亚组中均显示出了一致的IDFS获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初始不可手术、HR-、新辅助治疗后腋窝淋巴结仍呈阳性这部分高危风险的患者,T-DXd相较于T-DM1仍展现出显著获益。此外,与T-DM1相比,接受T-DXd治疗的患者,其远处复发(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复发)和局部区域复发的发生率都更低。

图2 DB05研究的主要研究终点结果

图3 DB05研究的IDFS亚组分析结果
关键次要终点DFS方面,T-DXd组的3年DFS率亦显著优于T-DM1组(92.3% vs 83.5%;HR=0.47;95%Cl 0.34-0.66;P<0.0001)。DRFI分析显示,T-DXd组和T-DM1组的3年DRFI率分别为93.9%和86.1%(HR=0.49;95%Cl 0.34-0.71)。在BMFI方面,两组的3年BMFI率分别为97.6%和95.8%(HR=0.64;95%Cl 0.35-1.17)。目前OS数据成熟度仅2.9%,但已显示出一定获益趋势,T-DXd组和T-DM1组的3年OS率分别为97.4% vs 95.7%(HR=0.61;95%Cl 0.34-1.10)。两组均有超72%的患者完成14个周期的治疗。T-DXd整体安全性可控,尚未出现新的安全信号。在需特别关注的间质性肺病(ILD)方面,主要为1~2级,≥3级ILD发生率仅为1.1%,临床通过适当的监测和及时干预,这种风险是可控的。

图4 DB05研究的关键次要研究终点结果

图5 DB05研究的DRFI、BMFI和OS结果
DB05研究对HER2+早期乳腺癌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对于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non-pCR)的患者,T-DXd有望为其在以治愈为目标的治疗过程中,提供更高效的治疗新选择。
龚畅教授
T-DXd在DB05研究中展现出的优异数据,无疑为其在早期HER2+乳腺癌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坚实循证依据。这一突破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临床路径。目前,针对新辅助治疗后non-pCR的HER2+乳腺癌患者,我们有哪些标准辅助强化策略?现阶段还面临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DB05研究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将对HER2+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治疗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兆基教授
在HER2+乳腺癌的治疗领域,从新辅助到辅助治疗阶段,多年来缺乏新的治疗方案,而本次ESMO大会上公布的DB05研究数据将对临床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目前,针对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non-pCR患者的标准治疗主要基于2019年KATHERINE研究的成果[5],该研究显示T-DM1的3年IDFS率为88.3%,较对照组的77%提高了11.3%(HR=0.50;95%Cl 0.39-0.64;P<0.001),并因此改写了临床指南。随后在202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8.4年随访数据显示[6],T-DM1组的7年IDFS率达到80.8%,相较于对照组提升了13.7%(80.8% vs 67.1%;HR=0.54;95%Cl 0.44-0.66);同时OS数据也显示T-DM1组为89.1%,对照组为84.4%,死亡风险降低了34%,进一步巩固了T-DM1在non-pCR患者中的标准治疗地位。此外,ExteNET研究支持对于淋巴结阳性等特定亚组患者,在曲妥珠单抗治疗后序贯一年奈拉替尼,可进一步降低30%的5年复发风险,并在2023年St.Gallen专家投票取得了超过60%专家认可,为部分患者提供了辅助强化治疗的选择[7-9]。
然而,KATHERINE研究也揭示出T-DM1的局限性:7年IDFS率80.8%意味着约20%的患者会在7年内复发,且亚组分析显示在初始不可手术、HR-或新辅助后淋巴结阳性的患者中,其疗效远低于总体人群。同时HER2+是早期乳腺癌患者脑转移的独立风险预测因素,其风险是HER2-患者的2.6倍[10]。KATHERINE研究的亚组分析结果也显示,T-DM1未能显著降低中枢神经系统复发风险,脑转移作为首次复发部位T-DM1组较对照组更为常见(5.9% vs 4.3%),提示T-DM1的预防脑转移疗效有限[11]。
DB05研究则针对这些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纳入了术前不可手术、HR-以及新辅助后淋巴结仍阳性的患者,并显示T-DXd在亚组分析中疗效优于T-DM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T-DXd的3年BMFI达到97.6%,较T-DM1组降低了36%的中枢神经系统复发风险,为预防脑转移提供了更有效的选择。总体而言,DB05研究秉承了在早期阶段使用高效药物以追求根治的理念,有望进一步降低早期乳腺癌的复发风险并提高治愈率,基于其突破性数据,T-DXd有望推动临床指南革新,成为新辅助治疗后non-pCR患者的新治疗标准。
龚畅教授
随着T-DXd在辅助治疗阶段取得的研究突破,其在早期乳腺癌全程管理中的战略定位就值得更前瞻的布局。结合DESTINY-Breast11(DB11)、EXTEND等其它早期领域的研究结果,未来T-DXd在早期乳腺癌治疗领域还有哪些值得探索的方向?
李杰
教授
DB11研究是ADC在HER2+乳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首个取得阳性结果的III期研究,其结果显示T-DXd序贯THP方案在高危HER2+乳腺癌患者(包括cT3以上、N0-N3分期及炎性乳腺癌)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达67.3%,显著优于对照组ddAC-THP方案的56.3%,且在HR+和HR-亚组均观察到一致改善趋势,证实该方案为高风险HER2+乳腺癌患者提供了一种疗效更优、毒性更低的选择[12]。与此同时,EXTEND研究正在积极探索T-DXd在中危T2N0患者中新辅助治疗的价值[13]。基于当前证据,T-DXd在早期乳腺癌的应用已从新辅助延伸至辅助治疗,为支持其在不同临床场景应用积累了重要循证依据。
未来T-DXd在早期乳腺癌治疗领域值得期待的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后续治疗决策,根据《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4年版)》,对于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的患者,建议完成时长1年的曲帕双靶抗HER2治疗;对于新辅助治疗后non-pCR的患者,建议术后T-DM1单药辅助治疗;当T-DM1未可及时,可以考虑加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奈拉替尼辅助强化治疗[14]。对于接受T-DXd-THP新辅助治疗后达到pCR的患者,后续治疗如何选择,是否可以继续使用T-DXd?而non-pCR的患者后续治疗策略的选择;以及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中高危患者直接使用T-DXd进行辅助治疗的可行性,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其次,拓展适用人群方面,DESTINY-Breast04(DB04)等研究已证实T-DXd对HER2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有效[15,16],未来可探索其在HER2低表达早期乳腺癌中的应用,明确其在该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为更多患者提供治疗选择。此外,联合治疗策略的探索也至关重要,T-DXd与免疫治疗、内分泌治疗等不同作用机制药物的联合使用是否会进一步提高疗效,降低复发风险,仍值得我们期待。最后,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也是未来研究的关键方向。目前尚缺乏可靠的预测T-DXd疗效的生物标志物,未来需深入研究HER2表达水平、基因突变状态、肿瘤微环境等因素与T-DXd疗效的关系,精准筛选最可能从T-DXd治疗中获益的患者,以尽早、最大化T-DXd的治疗获益。
龚畅教授
随着T-DXd治疗线序的不断前移,我们必须以全局视角重新审视HER2+乳腺癌的全程管理策略。DB05、DB11等早期领域的研究将会如何影响HER2+乳腺癌晚期治疗策略的选择?对于在早期阶段已经接受过T-DXd治疗的患者,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又应如何考量与布局?
兆基教授
DB05、DB11等早期乳腺癌领域的研究将对HER2+乳腺癌晚期治疗策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HER2+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基于CLEOPATRA研究的THP方案及PHILA研究的pyTH方案[17,18],而今年ASCO大会公布的DB09研究数据显示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超过40个月[19],进一步巩固了T-DXd在晚期一线治疗中的关键地位,并有望推动权威指南的更新。本次ESMO大会公布的DB05和DB11研究数据,或将进一步将T-DXd前移至早期阶段应用,这将导致晚期患者中出现更多在早期新辅助或辅助治疗中已使用过T-DXd的人群。针对这部分人群,晚期一线应如何选择治疗——是选择THP、T-DXd还是pyTH等方案,目前尚缺乏充分的临床证据,亟待进一步探索。
在制定晚期后续治疗策略时,需综合考量患者既往用药史和抗HER2治疗的敏感性和耐受性、肿瘤负荷等因素。此外,吡咯替尼、奈拉替尼、图卡替尼等小分子TKI药物因作用机制与ADC药物不同,可作为T-DXd后线治疗的潜在选择;而对于多线治疗后、距离早期T-DXd使用时间较长且一般状况良好的患者,也可考虑重新使用T-DXd。
龚畅教授
DB05研究的成功不仅仅是T-DXd取得的胜利,更是治疗理念的升级——即通过最有效的药物前移,最大程度地提升治愈希望。同时,这也要求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具备动态、全局的视野,将不断涌现的新证据有机地整合到患者的全程管理路径中,在追求最高治愈率的同时,谨慎权衡疗效、安全性与后续治疗选择的平衡,从而为患者制定最优的个体化治疗策略。
专家简介

龚畅 教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逸仙乳腺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教授三级 /二级主任医师 外科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乳腺诊断专科主任 乳腺肿瘤中心第二职工党支部书记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整合防筛专委会常委银铺子配资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委会 常委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专委会 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肿瘤医学学组组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乳腺专科医师分会副主委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分会癌症早筛早诊分会副主委
广东省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泛家族遗传性肿瘤防控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乳腺癌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常委
主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组长) 1项、国家科技创新20230(课题组长)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省部级基金7项。CSCO基金2项。入选科技部、教育部、广东省杰青等人才项目5项。主编人卫出版社专著《组织标记在乳腺疾病精准诊疗中的应用》。研究成果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获专利12项。以通讯(含共同)在
BMJ,Cell Reports Medicine,Med, Molecular Cancer,Advanced Science,等发表论文35篇,总引用2771次,高被引论文4篇。
专家简介

李杰 教授
博士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院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甲状腺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青年常务委员、甲状腺专委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乳腺学组 ( CSOBO)/中国抗癌协会乳腺分会(CBCS)青年专家组成员
广州市医师协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药学会肿瘤全程管理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
广东省预防学会乳腺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健委高层次人才评审专家 /广东省高层次人才评审专家
哈佛大学麻省总院( MGH/MEEI)、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访问学者
近年来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包括
NEJM(editorial letter),Nature Cancer,MC×2,STTT,CDDiff×2,Adv Sci,JAMA SURGCancer research,Oncogene×2,JTM等。
担任 STTT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Med Comm、Cancer、The Breast、Cancer Medicine、Gene、Endocrine、Oncotargets and Therapy 等杂志特邀审稿人。主编、参编或参译专著8部,近年来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金十余项。
专家简介
过兆基 教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 主任医师
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乳腺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防治与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肿瘤表观遗传研究与转化协作组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会第三届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乳腺疾病分会苏南乳腺疾病协作组组长
江苏省社会办医疗协会甲状腺乳腺专委会常委兼秘书长
江苏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乳腺外科学组委员
苏州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1]Charles G,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vs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in patients (pts) with high-risk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positive (HER2+) primary breast cancer (BC) with residual invasive disease after neoadjuvant therapy (tx): Interim analysis of DESTINY-Breast05. 2025 ESMO LBA1.
[2]Ahn S, et al. HER2 status in breast cancer: changes in guidelines and complicating factors for interpretation. J Pathol Transl Med. 2020;54(1):34-44.
[3]Masuda N, et al. A randomized, 3-arm, neoadjuvant, phase 2 study comparing docetaxel + carboplatin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 (TCbHP), TCbHP followed by trastuzumab emtansine and pertuzumab (T-DM1+P), and T-DM1+P in HER2-positive primary breast cancer.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20;180(1):135-146.
[4]Geyer CE Jr, et al. Survival with Trastuzumab Emtansine in Residual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5;392(3):249-257.
[5]von Minckwitz G, et al. Trastuzumab Emtansine for Residual Invasive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19;380(7):617-628.
[6]Geyer CE Jr, et al. Survival with Trastuzumab Emtansine in Residual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5;392(3):249-257.
[7]Chan A, et al. Neratinib after trastuzumab-based adjuvant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ExteNET):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6;17(3):367-377.
[8]Martin M, et al. Neratinib after trastuzumab-based adjuvant therapy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ExteNET): 5-year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17;18(12):1688-1700.
[9]St.Gallen Inter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nference. https://www.oncoconferences.ch/events/sg-bcc-2023/.
[10]Azim HA, et al. Predicting Brain Metastasi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Stage Versus Biology. Clin Breast Cancer. 2018;18(2):e187-e195.
[11]Mamounas EP, et al. Adjuvant T-DM1 versus trastuzumab i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invasive disease after neoadjuvant therapy for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subgroup analyses from KATHERINE. Ann Oncol. 2021;32(8):1005-1014.
[12]Nadia H, et al. DESTINY-Breast11: Neoadjuvant trastuzumab deruxtecan alone (T-DXd) or followed by paclitaxel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 (T-DXd-THP) vs SOC for high-risk HER2+ early breast cancer (eBC). 2025 ESMO 291O.
[13]T-DXd Versus THP for Medium-risk HER2-posi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ClinicalTrials.gov ID: NCT06548178.
[14]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等.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4年版)[J].中国癌症杂志,2023,33(12):1092-1187.
[15]Modi S,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in Previously Treated HER2-Low Advanced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2 Jul 7;387(1):9-20.
[16]Curigliano G.,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vs physician’s choice of chemotherapy (TPC) in patients (pts) with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R+),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low or HER2-ultralow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BC) with prior endocrine therapy (ET): Primary results from DESTINY-Breast06 (DB-06). ASCO 2024. Abstract LBA1000.
[17]Swain SM, et al. Pertuzumab, trastuzumab, and docetaxel for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LEOPATRA): end-of-study results from a double-blind,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Lancet Oncol. 2020 Apr;21(4):519-530.
[18]Ma F, et al. Pyrotinib versus placebo in combination with trastuzumab and docetaxel as first l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HILA): randomised, double blind, multicentre, phase 3 trial. BMJ. 2023;383:e076065.
[19]Sara M,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 pertuzumab (P) vs taxane + trastuzumab + pertuzumab (THP) for first-line (1L) treatment of patients (pts) with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positive (HER2+) advanced/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a/mBC): Interim results from DESTINY-Breast09. 2025 ASCO LBA1008.
*此文仅用于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平台立场。
盈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